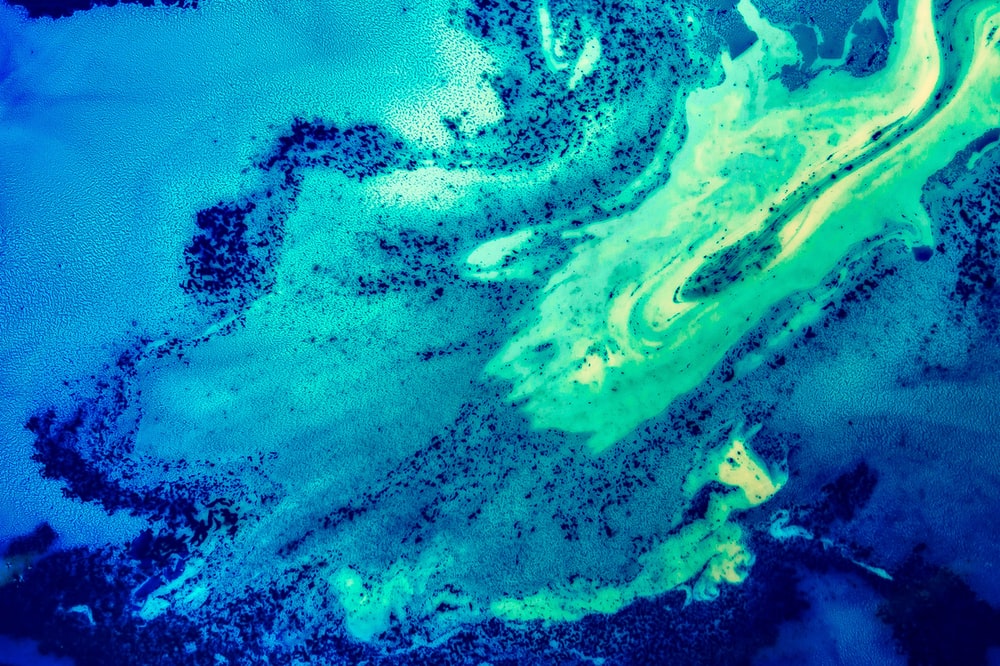我不能開始算我求我媽,讓我獲得了日本頭髮拉直處理的時間。如果我猜的話,它很可能是幾百個,但我的努力都無濟於事。她關注的是,有一天,我會改變我的想法,這將是為時已晚,以扭轉做我的頭髮的損害。她是對的,但是這將是近十年之前,我終於學會了欣賞我的捲髮。
目前我WASPy威徹斯特小學,只有為社會所接受的髮型是針直。我融入其中,並且是完全做頭髮,直到我12歲時和青春期打了我的頭髮辣妹去瘋狂辣妹速度比我可以說“鋸齒A-鋸齒啊。”整潔是出於和獅子的鬃毛是,但不是任何人的審美標準。我厭惡是不同的,並且感到新的頭髮前沿嚇倒,我似乎理解不能,不管硬我怎樣努力。
我的新興猶太人來回-A基因的傳家寶從我的猶太父親,湧現出不那麼巧妙地在我的劉海的第一個跡象。隨著我的荷爾蒙肆虐,我要求的答案,所以我做了任何困惑的年輕女孩會做,問我媽媽的幫助。(我爸爸的首選護髮技術是其凝膠就範,這是不是我的肩膀長度剪一個可行的選擇。)雖然她的多才多藝的女人,我的媽媽是亞洲,並永遠只風格針直發,這樣處理我的不羈拖把,這是她的對立面不在其中。這並不是說我們沒有嘗試。發膠,捲曲霜,抗毛躁血清,你的名字。不過,每次我去了本地的沙龍理髮的時候,我會離開看起來像一棵聖誕樹。相反,分層和稀疏的頭髮出的,造型師將保持長期股,離開我的頭髮看起來笨重和三角。我整天在家裡生悶氣和我爸對我身上賜予他的捲髮,外的控制毛髮定期嗤之以鼻。
我在早期aughts最佳造型方法是確保我捲髮面取景劉海與蝴蝶夾,一個在我臉上的每一側,掖股進入我的直發。在中學,我就扎我的頭髮回到一個低馬尾,當我沒有用扁鐵油煎,青少年舞蹈通常之前。由於整個鎮上唯一的猶太亞洲,我的頭髮讓我感覺像一個幾乎被遺棄,我拼命地想看看其他人一樣。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我的觀點是狹隘的,沒有人在意思考為什麼直發似乎佔據統治地位,相對於其他材質和樣式。
學習愛我的頭髮是一個情感過山車。
在UPS並不多見之間,以及起伏是野蠻。在過夜的,我的朋友交換彼此的頭髮,我不能遠程涉及到的故事。我的辮子是凌亂和蓬頭垢面;他們總是顯得質樸。在夏季的幾個月,我會避免把我的頭在水下池,恐怕我拉直秀發弄濕和野生。它不只是頭髮要么。放學後,我的同學大部分將在基督教教義的幫會參加宗教課程,因此我想通過自己去拖和看電視家庭捲髮。
最後,我離開家鄉,來到紐約市,一個快速的火車車程,但另一個世界的多樣性方面,學院特別關於髮型。我與其他猶太人朋友誰擁抱他們的天然鎖,更重要的是,知道如何削減和照顧他們。我的課外活動成為發現絲綢枕套的美德,如何在一個鬆散的髮髻睡覺可以減輕毛躁,以及它為什麼必須請求短層和造型師(呼喊出輻條威爾給了我第一個適當的髮型)變薄。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我離開髮廊那災難性的一天,後來,在洗澡的時候,當時我就覺得分量十足的我濃密的頭髮已經奇蹟般地舉起我進入興奮狀態。
現在,二十年過了青春期,稍微成熟,我是誰,我幾乎沒有拉直我的頭髮內容。相反,我選擇穿它自然盡可能多地。更重要的是,很多人我知道是誰了日式化學拉直的過程中永久性地破壞了他們的捲髮。儘管所有我的青春期焦慮,我永遠感謝我的媽媽關閉了我的請求日本直。作為猶太人說,這是bashert(這是意第緒語的“的意思是”)。